
崔国斌,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主任。
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依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自己采取了保密措施,被告有接触机会且使用了相同的信息之后,就推定案涉信息具有秘密性及被诉侵权人具有不当利用行为。上述关于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明显降低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增加了涉嫌侵权人的举证义务,这一改动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很大震动。今天知函博士请到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学专家清华大学法学院崔国斌教授就《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接受采访,希望对读者有所裨益。
知函博士:崔老师您好,很荣幸邀请到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我们想请您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新增32条就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为此,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
崔国斌教授:嗯,好的。
知函博士: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秘密性和不当行为的证明很困难,被认为是造成权利人维权困难的重要原因,学术界也一直有意见呼吁改革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降低商业秘密权利人的举证难度,提高其维权积极性。因此,关于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明显降低商业秘密权利人举证责任的规定,国内众多学者表示支持,对此您怎么看?
崔国斌教授:我对秘密性和不当行为的证明责任推定规则持质疑态度。依据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20年初达成的《中美经济贸易协议》,在原告和权利人证明部分相关事实后,法律就推定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同时被告具有不当行为。这一制度规定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负担,但也不合理地加重了弱势被告的负担,会产生过高的社会成本。决策者应当接受民事诉讼领域主流理论的指引,坚持让商业秘密权利人承担证明责任,重申合理的证明标准,为权利人履行举证义务提供更具体的指引。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符合中国长远产业利益的合理的商业秘密诉讼制度。
知函博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第一款规定,“在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审判程序中,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已经对所主张的商业秘密采取保密措施,且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权利人所主张的商业秘密不属于本法规定的商业秘密。”您认为,这一规定是否可以理解为原被告双方证明责任倒置?
崔国斌教授:我认为上述法律规定不属于证明责任倒置。依据上述第32条,在原告证明“秘密性”和“不当行为”的部分相关事实后,法律推定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或存在不当行为,然后再由被告承担举证义务来提供反驳证据。这与秘密性或不当行为方面的证明责任倒置,有明显的差别,毕竟原告还是要证明一小部分相关事实,然后才有法律推定。因此,我认为可以按照民事诉讼领域的一般见解,将上述法律修订后的安排表述为“法律对事实的推定”,而不采用“证明责任倒置”或“证明标准降低”的说法,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
知函博士:根据北京高院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在以判决方式审结的案件中,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未获得司法保护的210件案件中,法院认定不构成商业秘密的比例占67%。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原告主张保护的客体不构成商业秘密是其败诉的主要原因,这可能意味着秘密性证明责任存在问题。即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作为一项消极事实,证明起来存在一定难度。国内部分学者因此认为,应该将证明责任倒置给被告一方,对此您怎么看?
崔国斌教授:我认为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的困难程度还未达到应该代之以法律推定或倒置证明责任的程度。同时,法律推定或倒置证明责任对于被告利益和公共政策目标的影响也被低估。
首先,关于原告的证明难度。依据前文所述实体法标准,原告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这一消极事实时,需要证明两项事实,即诉争的商业秘密不为公众所知,也不容易获得。理论上,权利人要证明这一事实,必须找到检索所有能够获得的数据库,全面了解专业人员能够正常接触的商业实践,尝试各种独立研发或反向工程的路径,然后宣称诉争信息不为公众所知,也很不容易为公众获得。按照这一证明思路,权利人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自然非常困难,成本高昂。相反,被告要否认秘密性似乎很简单,只要指出其所掌握的该信息的公开来源就可以。两相对照,在很多人看来,双方举证难度差别巨大,为节省社会资源,将举证责任倒置或进行法律推定似乎是合理的选择。这应该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的法律推定得到部分学者支持的原因所在。
但事实上,民事诉讼法并不要求权利人按照上述方式和标准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要件。在被告没有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原告为了初步证明自己的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仅仅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委托相关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技术人员说明诉争的商业秘密的获取或研发过程,提供初步的独立研发或收集的证据;基于上述人员所熟悉的行业实践,说明诉争信息通常所处的状态;检索相关人员常用的数据库或网站,确认没有检索到相同的信息;基于上述人员所熟悉的商业实践,确认该信息未被公开使用;基于上述人员所熟悉的研发或反向工程思路,说明研发或反向工程的难度,排除很容易就获得该商业秘密的可能性,等等。受权利人委托,相关专业人员适当准备后都应该能够就上述问题提供证词和配套的初步证据。在这些初步证据的基础上,法院应该有能力评估诉争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的可能性。
在回到合理的证明标准之后,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即使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是消极事实,初步证明它也并不复杂。在多数情况下,原告无须大费周章就能完成任务。比如,产品配方是典型的商业秘密,只要原告能够举证证明自己所在的行业具有不公开新产品配方的习惯,而自己有实质性的研发投入和明确的商业计划,并在经营中将它确认为秘密并采取保密措施,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就应该确认该产品配方属于商业秘密。这时候,原告甚至无须进行复杂的公开媒体或专业数据库的检索工作,就能够完成自己的初步证明责任。如果被告提出质疑,再由被告来质证。
与权利人证明秘密性并不十分困难相比较,被告否认秘密性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被告要否认诉争信息的秘密性,要证明该信息属于所谓“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能够通过观察产品或反向工程很容易获得”“被公开使用过” 等。这些虽然属于积极事实,但是要真正拿出确凿的证据说服法官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记载诉争信息的公开出版物一般并不存在,否则,原告自己在准备诉讼时,就会发现这些破绽,也就不会提起诉讼了。
从以上分析看,在合理的证明标准下,商业秘密的秘密性的证明,对于权利人可能稍微困难一些,但并不存在实质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于被告而言,除非是在已有文献公开了商业秘密的简单案例中,否则,要提供证据否定秘密性也并不容易。综上,原被告之间在举证成本上的差距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倒置举证责任并没有迫切性。
知函博士:所以您认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秘密性的证明责任仍应当由权利人承担?
崔国斌教授:是的,并且我认为,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中,秘密性初步证明的法律标准,与普通民事侵权领域的证明标准应该是一样的,并不需要刻意地降低。
知函博士:好的,那么在您所持有的秘密性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和证明标准的前提下,您认为商业秘密权利人应当从哪些方面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呢?
崔国斌教授:权利人在证明商业秘密的秘密性时,通常可以从相关的行业习惯、诉争信息的获取方式和特点、权利人的投入、权利人所采取的保密措施、专业人员的认知等方面努力,帮助法院形成秘密性的新证。
第一,证明本行业中对于案涉信息具有保密习惯。不同行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态度和做法不尽相同。如果原告能够证明特定行业存在普遍的保密习惯,则对于法官推定争议的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有直接的帮助。比如,在北京一得阁墨业有限责任公司诉高辛茂案中,原告让法院相信,墨汁企业对墨汁配方进行保密并不断改进,符合市场规律和实际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法院更倾向于接受原告的配方具有秘密性的主张。
第二,证明技术信息的获取方式和内容特点。从信息本身的获取方式和内容特点中,法院实际上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关于该信息秘密性的心证。当然,不同类型信息具有秘密性的可能性也有很大差异。企业在正常研发过程中获得的技术方案信息,在采取保密措施的情况下,通常都具有秘密性。对于经营信息,如果企业能够说明收集、加工和整理的过程,通常也很容易就能推断最终信息具有一定的秘密性。而企业从公开渠道收集的经营信息是否具有秘密性,则存在较大的疑问。
第三,证明获取诉争信息投入较大。商业秘密的秘密性不仅要求不为公众所知,而且还要求不容易获得。如果原告说明自己获取商业秘密的过程之后,证明其为获得商业秘密付出实质性的劳动、金钱和努力,则可以帮助法院评估该信息是否容易获得,进而评估其秘密性。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原告通过合理的方法取得该信息并不容易,则通常被告也不会从公共领域很容易得到诉争信息。
第四,证明采取了保密措施。理论上,权利人的主观认识或保密措施与相关信息是否事实上处于秘密状态,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在争议发生之前,权利人对相关信息采取具体的有针对性的保密措施,能够帮助法院推断该信息的秘密性。这是因为该权利人事前对信息的秘密性的认知。另外,作为保密措施的一部分,权利人事前可能要求被告特别确认某些信息为商业秘密。这一事实一般足以推定该商业秘密具有秘密性。比如,原单位要求其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的,足以证明企业和员工对于保密协议中保密信息秘密性的认同和确认。
第五,提交专业人员意见。在民事诉讼中,权利人提交相关领域专业人员的证词,说明商业秘密产生的商业或技术背景,证明通过合理检索和其他努力并没有从公共领域获知相同信息,是证明秘密性的常见做法。
知函博士:《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第2款规定,“商业秘密权利人提供初步证据合理表明商业秘密被侵犯”,而且“有证据表明涉嫌侵权人有渠道或者机会获取商业秘密,且其使用的信息与该商业秘密实质上相同”的,则“涉嫌侵权人应当证明其不存在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对此规定,您作何评价?
崔国斌教授:我认为,这一法律推定事实的规定会在多个方面给被告带来压力。这里以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中占最大比例的雇员跳槽类纠纷来说明。
首先,被告和他的新雇主在提供反证的过程中,要被迫披露自己研发过程或经营管理过程中的很多商业秘密。在商业秘密诉讼中,即便证据涉及商业秘密,依然要进行交换和质证。 因此,商业秘密在诉讼程序中会不会二次泄露,是双方普遍关心的问题。理论上,法院可以要求参与诉讼的各方签署保密协议。但是,实际上,各方很难真正彼此信任。对于被告而言,自己的秘密被更多的人知道,风险就大大增加。这导致一些当事人宁可败诉也不提交技术资料。这一现象,在过去的案例中已经有所体现,在证明责任尚未倒置的情况下,就有很多权利人为了利用举证和质证程序获取被告的商业秘密,恶意提起诉讼了。因此,为了避免被告的商业秘密因为诉讼而受到损害,不能实行证明责任倒置,这一立场应该被坚持到底。
其次,在侵权诉讼判决之前,被告并不清楚自己的证据是否足以否定前述秘密性和不当行为的可能性,作为理性的诉讼主体,被告会做最坏的打算,还会提供其他能够否定侵权指控的证据。比如:原告未采取保密措施;自己在新雇主处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以切割他和诉争秘密的联系;新雇主产品与原告产品之间的联系;新雇主独立研发产品的过程等;新雇主与第三方的许可或合作关系,等等。显然,提供这些证据都会实质性耗费被告的诉讼资源。在权利人的商业秘密并未经过法定的程序确权,权利人也没有证明秘密性和不当行为的情况下,让被告承担这些举证成本,很有可能让权利人产生恶意利用诉讼的动机,利用诉讼程序迫使被告做出不合理的让步。
再次,商业秘密侵权事实的法律推定与促进人才流动的公共政策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在雇员离职后,企业常常担心竞争对手从雇员的知识或技能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即便没有证据证明雇员侵害商业秘密,也希望阻止此类事情发生,为此企业可能要求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作为应对,我国法律对于竞业禁止有严格限制,使之在有限的范围内有效,并要求对员工给予合理补偿。从中可以看出立法者对于员工择业自由的重视。而在离职雇员没有前述竞业禁止协议的情况下,雇主很有可能利用商业秘密侵权诉讼来给离职员工和新雇主找麻烦,从而使得新雇主认为该员工是个负担而不是资产,不敢让该雇员从事相关的工作;同时,这也会吓阻企业其他员工仿效该员工离职。
最后,不当行为的法律推定会普遍增加企业管理成本。由于企业之间人才流动非常普遍,潜在的可能成为被告的企业会为了避免不可预见的商业秘密诉讼的困扰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将自己的科研和经营活动文献化,以便一旦被诉侵权,可以随时拿出可靠证据证明自己独立的技术研发或信息收集过程。这样一来,社会的整体成本势必要高过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的传统方案。我认为,面对那些担心不当行为举证困难的权利人,社会应鼓励他们聘用更为可靠的工作人员,采取更为严密的保护措施,约定更为严厉的违约责任,等等;而不是相反,要求数量更多的可能成为被告的企业来配合该权利人,普遍增加管理投入以确保能够赢得将来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
注释:本采访的大部分观点来源于崔国斌教授发表在《交大法学》2020年第4期的专业文章《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一文,读者可以阅读参考。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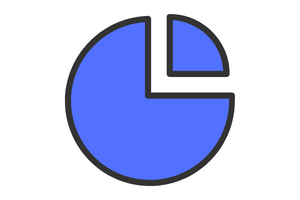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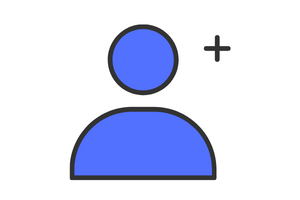



 刘知函律师创办了“知函博士商业秘密访谈”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定期分享商业秘密领域与知识产权犯罪领域原创研究成果,感兴趣的请关注。
刘知函律师创办了“知函博士商业秘密访谈”微信公众号自媒体,定期分享商业秘密领域与知识产权犯罪领域原创研究成果,感兴趣的请关注。


